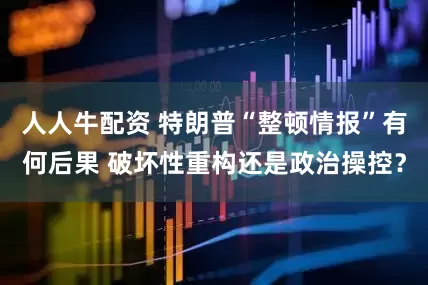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正着手调阅各大情报机构的内部邮件和聊天记录,试图借助人工智能手段挖掘出可能妨碍特朗普政策落地的人员与内容。
这一举动在美国情报界引发强烈反弹。多位资深官员认为,这种筛查方式变相成了“政治审查”,是对机构内部持不同声音者的清算。表面上打着“去政治化”的旗号,实则是在通过换人和操控评估结果,把情报系统变成服务总统政治议程的工具。

作为特朗普的首席情报顾问,加巴德被赋予监管整个美国情报体系的权力——涵盖18个独立机构。然而,她并未展现出守护情报机构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姿态。多起报道显示,她曾要求下属“修正”那些不利于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评估结论,甚至直接解雇不愿配合的高级分析官。
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如果情报系统开始将对总统的忠诚凌驾于对事实的忠诚之上,那么它将彻底丧失存在的意义,变质为政府的政治传声筒。这一幕,他不是第一次看到。
回顾历史,冯稼时曾领导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是当年唯一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出质疑的情报部门;而在2007年主导的对伊朗核计划的情报评估中,他的团队得出“德黑兰已于2003年叫停核武研发”的结论,一度颠覆了布什政府的外交路线,阻止了美国再次深陷战争泥潭。
然而今天,情报评估的独立性正在遭受严峻挑战。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提交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尤其是否定报告中关于伊朗核进展的判断,理由竟然是“她错了”,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这种轻率的否定让冯稼时感到震惊: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再基于证据做决策,那么再专业的情报分析也毫无价值。
冯稼时指出,情报工作不是学术研究,时间紧、信息碎片化,往往还相互矛盾。正因如此,情报分析师的职责不是“得出结论”,而是帮助决策者理解局势、掌握大概率趋势。在面对同一组信息时,不同机构因背景和职责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判断。过去的做法是让这些团队面对面地沟通,坦诚各自的分析假设,并尝试缩小分歧。但特朗普政府显然对这一套不感兴趣。
“历届政府即使有分歧,至少还是以事实为讨论基础。”冯稼时说,“但特朗普团队的做法根本无视现实,只在意是否有助于他们的政治目标。”
这种对情报系统的政治化干预,已损害其公信力和正常运行机制。情报部门之所以有别于外交口径、媒体话语和智库立场,正是因为它不带主观议程,靠的是海量数据和多维判断。它不是政客口中的“辅助辩词”,而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底层逻辑支持的系统工程。
冯稼时强调,一旦情报分析师意识到他们的判断将被公开、甚至扭曲使用,那他们在撰写报告时就会变得畏首畏尾,不再敢直陈要害。这不仅削弱了情报系统的效率,还使得高层决策者失去了唯一能提供全貌的渠道。
从“清洗”国家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到逼迫分析师“修改报告口径”,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已让情报界深感寒意。一个理应无党派、讲证据的专业系统,正一步步被拖入政治漩涡。
当年在伊朗核问题上,冯稼时带领的团队在最后一刻因新情报的出现改写了初稿。这种“及时修正”的勇气来自于对事实的敬畏。但今天,这种机制正在遭到破坏。
“只存在‘政策成功’或‘情报失败’这两种结论。”冯稼时用一句华盛顿的老话总结他多年来的从政经验。他强调,情报工作的使命从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明确当下我们知道什么、不了解什么,以及哪些判断有高度不确定性。真正成熟的政府,是愿意在不确定中做出负责任选择,而不是要求情报系统给出符合政治预期的“标准答案”。
当被问及特朗普政府为何在中东政策上出现自相矛盾时,冯稼时指出:特朗普一方面想降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负担,追求“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又试图遏制核武扩散,防止伊朗等国跨越门槛。然而,这两个目标天然冲突。打击伊朗核设施短期看或许是遏制手段,但长远看,反而会坚定伊朗“拥核自保”的决心,就像乌克兰放弃核武后却失去了安全保障。
此外,美国在中东的介入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冷战后的石油战略,到对以色列的道义责任,再到防止核扩散的全球安全考量,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早已盘根错节。特朗普的政策尝试回避历史重担,但现实又迫使其不得不重返战场。
冯稼时最后表示,特朗普团队中存在两种声音:一类想尽快抽身中东,另一类则希望维持美方控制力。但如果连情报基础都不再客观透明,战略选择恐怕注定无法明智。
情报的价值,从不是为了服务权力,而是让权力不至于偏离现实。而当这个基础被政治任性侵蚀时,不仅是美国的政策判断会失真,更将动摇全球对美国情报体系的信任根基。
亿融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